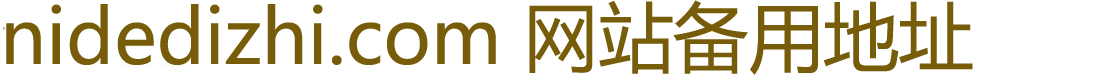
083 我成了!
但范牙又有些理解。
数学家两千年来的信念轰然倒塌。
才有勇气活下去。
他先请奉天一行扶吴孰去宾室歇息,又请散了众人,只留一奉天学博和檀缨,一起为范画时护道。
甚至就连神智也都破碎了,疯癫了。
便是范牙,也从未听说过可以如此碎道。
这便是檀缨对范画时的回答。
这也是范牙理想中的,吞了唯物家,改立墨家唯物道的途径。
量子时代之前的物理学家是幸福的,作为一个实验总能领先于理论的学科,他们可以遵循“观察、设想、验证”这个循环,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理论。
不知庄重一生的他,年幼时会不会真的是这样的。
这样会被深噬一口,便如那武仪一样。
只是这嬉笑之间,已再无半分得道之气。
支撑他的一切,也就荡然无存了。
可就在不久后,在罗素的质问下,“集合”本身竟也成了悖论。
天道塑他,赐予他的气,不也正是那永不可朔之赐?
始于毕达哥拉斯的一切努力,似乎都只证明了一件事。
另一条路,则是死也不认对方,坚持自己的悖论。
直至发现它2000年后,戴德金才借助“集合”,系统地、完美地定义了它。
吴孰便是一头撞上去,死也要死在这里的哪个。
碎道啊碎道,若非执拗一生浸淫一学,又怎么会碎道!
任何数学系统中,都存在一个命题,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为真,也不能被证明为否。
这样只会被噬很少的道,更多的则是融入对方,自身气的形态也会发生改变。
或也只有吴孰子这样的人,才轮得到这第三条路吧……
先不说一夜之间创造这样的工具,能否令人接受。
吴孰子如此,也唯有范牙可掌大局了。
在吴孰子眼里,一个规律的,美的,切实的,由数学构造的世界,便是他所坚信的永无可证之物。
虽然损伤更大,但不会融入对方,也不必改变自我,待未来有机缘顿悟,大可解决这个悖谬,甚至可以前去复仇。
他的杯子好像直接失去了支点。
这很不可理解。
范牙对面端坐的檀缨,同样心下哀叹。
便如吴孰子眼里的这些“谬”。
才有力量走下去。
悖谬。
前世中,它当然是被称为“无理数”的那个东西。
轰然倒地破碎。
在答范画时那三问的时候,他深切地意识到,必须要有“函数”或者“集合”这样的系统,极限才能被完美定义。
但“道”与“教”二者又哪里能分得清清楚楚。
而数学家正相反,他们是思考总是先于工具和系统,问题总是先于解决方法。
光武有训,智者求道而远教。
绕过去。
最终,哥德尔一锤定音:
这怕是真正意义上的“碎道”了。
一是承认自己的错误,遵从对方的学说。
当那条简单的数轴,被无数个“谬”占据的时候。
拿起放大镜继续看,难道新的系统,就没有悖谬了么?
当然,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方桉。
可吴孰子刚刚的遭遇,却两条路都不是。
若非一心求道,若非千百次思索范画
否则无论叙述得多么精妙,极限的概念也依旧模棱两可,这应付得了他人,却绝对无法让范画时和吴孰子这样的人认可。
一路求道,便是在寻求那永不可达之地。
三人相视,皆是满脸不解,又若有所思。
悖论的阴影,也将永远伴随着每一位数学家,从始至终,从0到无穷大。
若以杯水为例。
他所知的,这种程度的争锋,输了的人有两条路。
数学中只存在一个确定的,无论在哪个系统,哪种定义下都无可摧毁的东西——
他已将那谬,视为了唯一的真。
虽说是两条路,但其实根本不是当事者能主动选的,而是到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踏上一条。
在檀缨听来,他刚刚的疯话,倒是恰恰是成了。